今天是教师节,学校怕我们没事,就组织了学习开会,可惜我有事不能去。
是什么事呢?就是回忆,回忆“教师”吧。但中学到大学,特别是大学,“教师”二字简直是谈不完的甜酸苦辣,改日再叙,只说初中之前。
就从我出生讲起吧。
作为一只不幸的上海土鳖,投胎没有资格做精英,1979年疯子尼采(或者基佬米歇尔•福柯)诞辰纪念日那天的凌晨,我出生在凤阳路的长征医院。由于生产并不顺利,军医大夫们尽心尽力,产钳只在我脑门压出一小块凹痕,妈妈对子弟兵感恩至今。
我家就住在北京东路、新昌路,后来在西藏中路、凤阳路的外公家大概也住过一阵子,按照就近入读的原则,去了“红星托儿所”。红星啊,乌兰巴托般的名头,还没有褪去极左年代的风华。讽刺的是,托儿所设在江阴路一座洋房里。江阴路是当时市中心著名的花鸟市场,对面就是人民公园,游乐气氛丰足,据大人说,我常常哭闹不肯去托儿所,外公心软,趁爸妈不一道送我去托儿所,就把童车调转方向,带我看花鸟鱼虫去了。我游手好闲的病,也是那时惯出来的。
不久,落实政策,洋房还给了归国华侨,托儿所就地解散(很多年后,我路过江阴路,爸爸指给我看:“弄堂口搓大饼的那个阿姨,你还记得吗?是你们托儿所爱唱越剧的吴老师呀!”),我又去了一家附近的托儿所。读完,去了国际饭店后面的黄河路幼儿园。现在这家还在,改名“好小囡幼儿园”,匾是陈至立同志手书。上海不是很容易见到这位《辞海》现任主编的字。在幼儿园,发生了两件终身难忘的事。一件是追打过程中,摔断了左臂,送去对面长征医院绑了石膏(又是笑嘻嘻的老军医),伤快好时再去幼儿园,老师对我特别照顾,安排我单独睡床,优加看护(原来我和一个叫SL的女生很要好,午睡都是抱着她睡地板的,床有什么好睡的……)。另一件是最后上课那天,管我们班的梁老师、董老师说我们要去读小学了,小学的老师会和幼儿园的老师对我们一样好,甚至更加好,我却异常难过,舍不得她们,人生第一次。幼儿园午饭的酱汁红烧肉,滋味绝妙,三十年来无复品尝,终成一大怀恋。
之所以要说托儿所、幼儿园的劳什子,是因为那里的老师给我印象都很好,像妈妈,像姐姐,从来没有冷眼嘲讽,更别说打骂了,遇到我家人来接我,也都是好话相迎,夸我聪明。那时,我还坚信,社会主义的未来是美好的——今天更加坚信,呵呵。
小学我就不在黄浦区读了,因为1984年,爸爸单位分了新公房(今天上海叫“老公房”或“旧公房”),在很偏远的闸北区南部,步行到人民广场有近3公里的距离。房子就是我爸爸单位轻工业局建的,地基还挖出了明朝也不知是清朝的当官的棺材……初中历史老师告诉我,附近解放前很多乱坟岗。此外,还有上海滩鼎鼎大名的西宝兴路火葬场。那我小学就没法在黄浦读了,但妈妈不喜欢闸北,也不让我在闸北读,她就带着我去她单位所在区读:静安。
南京西路第二小学,今天看来是僵尸单炖一样的高冷存在。本部位于Westgate Mall对面梅龙镇酒家东侧的洋楼内,洋楼前的空地上,1986年9月1日,我站立40分钟,接受了入学教育。别的都忘了,反正是绿领巾啊,红领巾啊的,只记得两位高年级同学上司令台(就是防空洞入口顶部吧)表演相声,一点都不好笑。那时,很多男生的业余爱好就是下午5点听广播里的相声,6点半再听更精彩的单田芳评书连播,挺认同北方文化的,不像今天“大蒜邦”和“咖啡派”情绪这么对立。
我读的一年级有两个班,和二年级两个班,都在隔壁弄堂里的分部。这条弄堂我到最近才晓得,叫静安别墅。分部旧址开过文青圣地:2666图书馆。如果说梅龙镇的洋楼还比较宽敞,修修改改,做课堂挺好,那静安别墅实在是局促如弹丸。没有操场,早操只能在弄堂里做,看阿姨爷叔穿着睡衣睡裤提着菜篮子穿梭于我和班长中间。我什么长都不是,班长HCP是我这辈子第二个喜欢的女人——第一个是幼儿园的董老师,董老师今天看照片都是百里挑一的大美女,我毕业后,她和男友去了美国。我现在偶尔还会意淫和她在哈佛的某个角落邂逅,就像中年版永尾完治与雅诗兰黛ANP版赤名莉香那样,哈哈。啊呀,扯远了,继续说小学。
课堂就是民居,下课在天井里玩“老鹰抓小鸡”。二楼住着一位老医生,他和他老伴看我常常迟到,知道我有哮喘,叫我上楼,拿出电筒、压舌板、听诊器给我诊治。可惜,内不治喘,外不治癣,这是古话,但我感念他的热心,如还健在,应过百岁。我常常迟到,更多原因是因为当时上海市区交通极差,每次都要在路上耗费一个多小时,车厢里还特别挤,好几次幼弱的身体被大人们挤得悬在空中。常常在众目睽睽之下,灰溜溜敲开教室的门,走到最后一排坐下。放学,我得等妈妈下班接我,她就在附近的陕西北路、威海路上班,但学校三四点就放了,她有时要加班到五六点。班主任、教语文的张老师和教数学的蔡老师对我特别照顾,把我留在办公室——对面的民居,做作业,直到妈妈来接我,她们才下班。她们都劝我妈妈:这样没意思,耽误孩子学习。其实也没怎么太耽误,前十名还是有的,转学时大概是第三吧。前面落后些,是因为黄浦的幼儿园没教过拼音,而多数是静安生源的同学早学过了。蔡老师还来过我家,很热心地想帮我家“调房子”到静安一处石库门,但对方家里丈夫突然得了急病,遂作罢。
就这么在66路、18路、15路、20路等等公交车上,折腾了一年,妈妈终于认命,不要我接受“上只角”的教育了,同意我在闸北读书。但转学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吗?本质上,还是计划经济时代,什么都要“开后门”。“开后门”那个词,就是那年头流行起来的。
那年头,上海的轻工业业绩很好,热卖全国,爸爸在市级主管单位当个小干部,路子多,就托了人,辗转到闸北区某中心小学(下简称“某中心”)。转学前那个暑假,爸爸带我去参加特别组织的摸底考,好像就我一个人考,但有好几个老头看着我做卷子,连十二生肖都考,幸亏我幼儿园有条小手绢上印全了,背得烂熟。
第一次去某中心,是1987年暑假快结束时的返校活动。这是一所位于中兴路、宝通路的学校,虽然闸北是工业区加贫民窟,向为沪人鄙视,但某中心附近有基督教闸北堂(我幼儿园时,身为党员的爸爸带后来归心佛教的我参加过这里的圣诞弥撒)和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旧址,陈云同志战斗过的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也在附近,算是不学之地的人文荟萃吧。
返校,我谁都不认识,班主任把我介绍给全班,然后把其他人介绍给全班。原来我不是唯一转来的。返校的目的呢,是检查暑假作业和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是……是……是……是捡牙膏皮!!!谁捡得多,谁就是好苗苗。我回家就问妈妈:那些同学就不读书,不玩吗?为什么要捡牙膏皮呀?妈妈也不大懂。那年头,牙膏真是精贵的东西啊,牙膏皮何其难得?我初中第一次向女生表白,送的就是国内稀罕的Golgate牙膏。果然,不久发现了有同学为了多得牙膏皮,挤光了家里的牙膏,被大人痛骂,还告诉了老师。
班主任W老师呢,也是个美女。和董老师不同,她发型有点洋气,我甚至中学的春梦里都出现过她……数学沈老师则是个老太太了。我对W老师最初的印象还好。她粉笔字写得很工整,上课也挺生动,像电视里的燕子姐姐陈燕华。但不知为何,她对我有顽固的歧视,总是把我放学后留下来“练坐”。
“练坐”也就是暴力程度轻些的体罚。每天放学前,W老师会静静扫视一遍全班,报出须练坐者的名字。必须腰挺直,双手放于背后,至少这么坐一节课。罚“练坐”的理由很单一:上课捣乱。我是捣乱了,但我很快识相了,上课不乱说乱动了,怎么还要我“练坐”呢?老师的理由是:同学,你病得不轻,需要巩固巩固疗效。好吧。
很多年后,大概是我读大学了吧,有一天突然对妈妈说:“想我当年读书这么差,也能进复旦啊?人生真是太无常了。”妈妈问我怎么差了。我说高中考试都不及格啊,小学常常挨罚“练坐”啊。谁知她突然蹦出一句:“那个W老师?你知道她为什么要你天天‘练坐’吗?”“不知道啊!”“还不是为了你爸爸的票子!”我没有小伙伴,当时独自惊呆了。
原来,老师不是要我巩固,是全校有很多老师要洗衣机票子,要修洗衣机。洗衣机那时是紧俏的商品,凭票供应,而我爸爸调到洗衣机总厂了,为保障我在学校卑微的存在,他竟然向老师们另类的威胁服软了。
果然,后来不怎么叫我“练坐”,因为要多少票子,爸爸扯张白纸,写几个字就行。家里洗衣机坏了?没事,爸爸一个电话,第二天工人师傅就上门服务,包你修好,而且分文不取。不是不取,是不敢去,回头爸爸给。你取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钱,回头工程师就把我的灵魂给修理了,怎么得了?
但爸爸手上这点特权根本没有为我在校内地位的提升起到任何正面作用,有更大特权的家长还有好好几位。那时,谁家父是厂长,谁家母是书记,所有同学都知道。每到教师节、过年,教师办公室门庭若市。人家长都去,你家长能不去吗?可你家长要想只送本挂历,就免了吧,太寒碜,丢不起那人啊!妈妈就这样被“请”出过办公室,下详。
就在我自感适应某中心的节奏之际,W老师约见我妈妈,沉痛宣告:“你儿子太差了,从静安来我们闸北,学习完全跟不上,可能要留级或者退学,你们家长要做好思想准备。”后来妈妈告诉我,她回来路上就哭了。而我至今莫名其妙,我虽然没教养,不读书,可成绩真的不是最差的,一直保持中不溜秋,怎么就要闹到读不下去的份儿上了呢?实在是气场不合吧。
W老师治下,我特别爱打架,还吃过两次苦头。一次是后来发生的,我下课和小伙伴们去工地打架,我一颗石子飞出去——当时单田芳正说《白眉大侠徐良》——打破了我同学、教导主任之侄子的脑门,受力点就在右眼和右侧太阳穴之间。血流如注,我当时吓蒙了,以为会枪毙,结果没有。赔钱,人家不要,只收了两袋奶粉。高风亮节!这次呢,我认罪伏法,一人做事一人当。但另一次,早前发生的,是一群男生追打另一个学生,我是冤枉的。被追打的叫王菲,三年级去了香港,可惜是男的。王菲近视眼,慌不择路,一头撞在楼梯扶手上,撞破了脑袋。W老师无端认定我是主谋。呸!我当时跑在队尾,那些跑在前头的,她倒不问一词。后来,W老师把儿子带来班里玩,在我身边不小心摔倒,又怪到我头上。再后来,才貌双全的W老师高升,执掌其他学校去了。
我前面提到一位沈老师,不是没道理的。沈老师和其他好多老师不同的地方,在于她很少收礼。即便收礼,也一定还礼,至少等值。很真诚,甚至送到我家里来。爸妈后来也就不给她送礼了。我对某中心几乎没有任何好印象,除了她。她还是尊重学生和家长的,没有因为当了老师,拿起教鞭,就自命为特权阶级。可惜,这样的人,当时就很难得。我从教数年,每次学生来送礼,我都会想起忠厚勤勉的沈老师。
气场还不合的一处,是伙食。在南京路时,学校太小,没法开食堂,各自解决伙食。很多同学离家近,就回家吃,我太远了,也不能去妈妈单位吃——社会主义的企业有严格的规定吧——妈妈就托了关系,安排我到近水楼台的梅龙镇饭店吃。今天,梅龙镇和上海其他所有老字号一样,都衰败得不成样子(杏花楼除外,杏花有很多黄牛拉出的肥料,所以一花独秀,常开不败),可当年的梅龙镇是南京西路最有名的饭庄,生意极好,也做起了社会公益:给附近学生提供午餐搭伙。我在微博曾回忆过,午餐基本不错,菜都是大厨掌勺,有订酒水的吃鱼中段,我们就吃鱼头或鱼尾巴,米饭敞开供应,但安排我们吃饭的地下一层常常停电,也不止是那里,整条南京西路都有事没事就停电,商店点白蜡烛营业。有次吃鱼头,我不吃,服务员逼着我吃,否则不让我去上课,我咬了几口就抱着门口的石狮子狂吐。我此后再也没碰过鱼头。就是这样的美馔佳肴,养刁了我的胃口,吃不惯某中心食堂供应的午饭。
某中心的午饭,猪食都不如。我如今贪吃,就是因为那年头很难吃,不敢吃,吃不饱。奇怪的是,同学们个个狼吞虎咽,扫荡净尽。收饭盒的师傅每次看到我一口不动地还回去,就瞪我白眼,骂我,说我不珍惜粮食,不让我去上课。惊动了班主任,她就真的拿着饭盒,叫我去办公室,把饭盒放在暖气炉上,让我吃完了再去上课。可是,我本来就不爱上课啊,这样不是挺好嘛。最后,没辙,又叫我妈妈来学校。那天很多家长都来学校看孩子吃午饭,食堂烧得特别好,我第一次吃完某中心的午饭。后来,妈妈又突击考察了一次,看到我平时的午饭,回去跟爸爸说:“真的质量很差。”她当时是党的基层干部,现在是退了休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她什么都会,就不会说谎。差到什么程度?每一盒饭,都能挑出不下十条虫。饭盒是我们搭伙的人,每人交一个。我交了个新的不锈钢的。后来可以退伙了,我就第一时间去领回饭盒,领回个旧的铝的。
领回饭盒的那天,放学,刚出校门,见一大群哥哥姐姐模样的人手拉手,慢悠悠从门口的中兴路走过,还有人举着横幅,上书“同济大学”。这是我三年级的事。那阵子,上海群众活动也多,公交瘫痪,爸妈都没法坐车去上班。而我天天盼望学校散伙的中国梦,到底没有实现。只是老师问家长要东西的风气消停了些。大学看BBS,看FTP,才晓得首都很多细节,不胜唏嘘。多事之夏一过,一切定性,学校组织我们停课去生物实验室看CCAV播放的光荣镜头。回忆起来,整个民族就是从那时起,破釜沉舟地一切朝钱看了。我们也换了老师,班主任、语文老师是H1,数学老师是H2。
据很多家长说,H2是英俊潇洒极了,反正我对男色不敏感。但H2对我们很凶,上课经常骂学生“脑子坏掉了”、“恶戆——又恶又戆”、“黄鱼脑子”、“寿棺材”,我跟着他,迅速掌握了上海方言的多数俚语。这样的好老师,当然晋升也很快,后来还上过电视教课。他和有些同学住在一个小区里,同学做不出作业就去他家问。可惜好景不长,据传师母怒了。有回上面来调查学生对他的满意度,很多同学就写了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坐我后面的陆同学,写了他“上课不讲普通话”。调查的同志回去了,H2来了解情况。就有小人把陆同学写的内容,当场揭发了出来,惹得H2顿时变脸。这个揭发同伴以邀上宠的小人不是别人,就是我。所以,我的无耻,是有历史根基的。但,我,忏,悔,了。
H1老师一脸严肃,讲课认真,照片前几年上过本市大报。但处理问题比较僵化。当时,刚被撤去小队长的我和霸占学习委员一职的董同学是班里成绩最好的,为了女人也常常争风吃醋,被和我关系很要好的班长陈同学揭发——看,这股风气不是我一个人在玩啊——写了篇日记,大意是希望全班在他的治理下能保持和谐、稳定、繁荣,不希望我和董这样龙争虎斗下去。H1看了日记(喂,干吗要给老师看啊?),大怒,把我叫去,问了我一句话,字字印在我脑中:“实际情况和他写的有出入吗?”可是,我那么小,不懂什么叫“出入”啊!我糊里糊涂,答了个“没有”。H1立马叫我回教室去,从此对我再没好脸色,我开班会抖脚都要挨恶狠狠的骂。董同学一样没好日子过,但他毕竟是有官位的人,瘦死的骆驼。去年,在人人网上认识个学弟,他说,H1老师居然在课上批评他们不给她买KFC吃,听来不可思议。我毕业后还和同学去H1老师家玩了两次,因为离着很近。老师让我和他儿子打游戏。但妈妈知道了,不大开心,估计是因为送挂历吃了闭门羹。女人啊……前几年,有个苏北的朋友租了房子,在我家附近,叫我去玩。跑去一看,嚄,这不是H1老师家嘛!
这段历史斗争时期内,还发生了体育老师被炒鱿鱼的事,使得广大老师对职业操守问题有所警觉。那位老师,好像姓张,很喜欢打学生,比“练坐”痛快多了。我算耳光吃得少的,吃过一个,至今耳鸣不歇。其他同学,大概是回去的脸型像是首尔整过了,给家长联名告到学校,丢了饭碗。我是家长,我也气啊,平时你们要什么,我们给什么,不就是为了对我孩子好点吗?还打人,杜月笙也要灭了你啊!
那时,师范中专生还要来实习。有阵子,突然老师就消失了一样,全给师范生接管。我们班来了俩,胖的那个姓毛,瘦的那个姓章。姓章的很喜欢坐我后面的女同学,有一次我和邻桌男生打架,推翻了课桌,压到了这位女同学的脚面,女同学痛苦地大哭,章老师震怒,把我关进学校临时搭建的小黑屋,不让我回家。毛老师给我说了好几次情,他才傍晚放我回去。听说后来他们都没有做教师这一行,毛可惜了。
五年级,要毕业升初中了。送礼风又刮起来。也不知怎么的,同学间传得很快,说大队长家是邮电局的,给校长送了正版猴票,等等等等。为什么要送礼呢?当时有全市统一的升学考试啊。没错,可那年,我们班走运,教委在谢丽娟同志领导下,搞“小学全班整体直升”试验,选到我们。我们只有两个名额,一个去上外附中,一个去闸北当时唯一的市重点市北中学。名额给谁呢?最后,考下来,也巧了。大队长、班长、我三个人非但总分一样,是全校最高的285分(满分300),连语数外各门分数都一样。大队长去了上外附中,班长去了市北中学,我则“整体直升”去一家附近弄堂里的普通中学也。六年后,从上海中学毕业,再联系老同学,得知大队长去了上外,班长去了上大,想想我进复旦,也不算太差,心气便平复了些。
至于校长,收没收猴票,我当然不好说。但过了几年,竟因为经济问题,锒铛入狱,倒是同学甚至老师都在传的。我也没见她进提篮桥,也不好说什么。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舅舅家楼下,她当时正指挥一辆车停进车位,我和她一起坐了一段电梯。她当然认我不出。
本文纯属回忆,虽然我记性极好,但未必全部准确真实,权当教师节有个教书的说了番梦话,姑妄听之。
总的说来,从我个人的经历可以看出,教师队伍和社会上其他职业一样,有好有坏,不必神圣化。神圣化,是因为有人发不起好教师的工资,提不高好教师的地位,如此而已。读书人向往的“师道”是很高尚的,可惜人间难寻。这番道理,我很早领悟,所以从教之初,我就不接受“师”字。别人称我是老师,除在课堂外,一概谢绝,只称自己是“某某大学职工”。这不是我装逼,只是我对“师道”还寄托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而已。这里回忆的是我初中前的一些教育经历,一些人,一些事。我也是坐三望四的人了,杂事渐多,记忆衰退,早点写下,以免忘记。将来有谁研究改革开放后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问题,希望能对他或她有些零零碎碎的时代背景上的参考价值吧。
是什么事呢?就是回忆,回忆“教师”吧。但中学到大学,特别是大学,“教师”二字简直是谈不完的甜酸苦辣,改日再叙,只说初中之前。
就从我出生讲起吧。
作为一只不幸的上海土鳖,投胎没有资格做精英,1979年疯子尼采(或者基佬米歇尔•福柯)诞辰纪念日那天的凌晨,我出生在凤阳路的长征医院。由于生产并不顺利,军医大夫们尽心尽力,产钳只在我脑门压出一小块凹痕,妈妈对子弟兵感恩至今。
我家就住在北京东路、新昌路,后来在西藏中路、凤阳路的外公家大概也住过一阵子,按照就近入读的原则,去了“红星托儿所”。红星啊,乌兰巴托般的名头,还没有褪去极左年代的风华。讽刺的是,托儿所设在江阴路一座洋房里。江阴路是当时市中心著名的花鸟市场,对面就是人民公园,游乐气氛丰足,据大人说,我常常哭闹不肯去托儿所,外公心软,趁爸妈不一道送我去托儿所,就把童车调转方向,带我看花鸟鱼虫去了。我游手好闲的病,也是那时惯出来的。
不久,落实政策,洋房还给了归国华侨,托儿所就地解散(很多年后,我路过江阴路,爸爸指给我看:“弄堂口搓大饼的那个阿姨,你还记得吗?是你们托儿所爱唱越剧的吴老师呀!”),我又去了一家附近的托儿所。读完,去了国际饭店后面的黄河路幼儿园。现在这家还在,改名“好小囡幼儿园”,匾是陈至立同志手书。上海不是很容易见到这位《辞海》现任主编的字。在幼儿园,发生了两件终身难忘的事。一件是追打过程中,摔断了左臂,送去对面长征医院绑了石膏(又是笑嘻嘻的老军医),伤快好时再去幼儿园,老师对我特别照顾,安排我单独睡床,优加看护(原来我和一个叫SL的女生很要好,午睡都是抱着她睡地板的,床有什么好睡的……)。另一件是最后上课那天,管我们班的梁老师、董老师说我们要去读小学了,小学的老师会和幼儿园的老师对我们一样好,甚至更加好,我却异常难过,舍不得她们,人生第一次。幼儿园午饭的酱汁红烧肉,滋味绝妙,三十年来无复品尝,终成一大怀恋。
之所以要说托儿所、幼儿园的劳什子,是因为那里的老师给我印象都很好,像妈妈,像姐姐,从来没有冷眼嘲讽,更别说打骂了,遇到我家人来接我,也都是好话相迎,夸我聪明。那时,我还坚信,社会主义的未来是美好的——今天更加坚信,呵呵。
小学我就不在黄浦区读了,因为1984年,爸爸单位分了新公房(今天上海叫“老公房”或“旧公房”),在很偏远的闸北区南部,步行到人民广场有近3公里的距离。房子就是我爸爸单位轻工业局建的,地基还挖出了明朝也不知是清朝的当官的棺材……初中历史老师告诉我,附近解放前很多乱坟岗。此外,还有上海滩鼎鼎大名的西宝兴路火葬场。那我小学就没法在黄浦读了,但妈妈不喜欢闸北,也不让我在闸北读,她就带着我去她单位所在区读:静安。
南京西路第二小学,今天看来是僵尸单炖一样的高冷存在。本部位于Westgate Mall对面梅龙镇酒家东侧的洋楼内,洋楼前的空地上,1986年9月1日,我站立40分钟,接受了入学教育。别的都忘了,反正是绿领巾啊,红领巾啊的,只记得两位高年级同学上司令台(就是防空洞入口顶部吧)表演相声,一点都不好笑。那时,很多男生的业余爱好就是下午5点听广播里的相声,6点半再听更精彩的单田芳评书连播,挺认同北方文化的,不像今天“大蒜邦”和“咖啡派”情绪这么对立。
我读的一年级有两个班,和二年级两个班,都在隔壁弄堂里的分部。这条弄堂我到最近才晓得,叫静安别墅。分部旧址开过文青圣地:2666图书馆。如果说梅龙镇的洋楼还比较宽敞,修修改改,做课堂挺好,那静安别墅实在是局促如弹丸。没有操场,早操只能在弄堂里做,看阿姨爷叔穿着睡衣睡裤提着菜篮子穿梭于我和班长中间。我什么长都不是,班长HCP是我这辈子第二个喜欢的女人——第一个是幼儿园的董老师,董老师今天看照片都是百里挑一的大美女,我毕业后,她和男友去了美国。我现在偶尔还会意淫和她在哈佛的某个角落邂逅,就像中年版永尾完治与雅诗兰黛ANP版赤名莉香那样,哈哈。啊呀,扯远了,继续说小学。
课堂就是民居,下课在天井里玩“老鹰抓小鸡”。二楼住着一位老医生,他和他老伴看我常常迟到,知道我有哮喘,叫我上楼,拿出电筒、压舌板、听诊器给我诊治。可惜,内不治喘,外不治癣,这是古话,但我感念他的热心,如还健在,应过百岁。我常常迟到,更多原因是因为当时上海市区交通极差,每次都要在路上耗费一个多小时,车厢里还特别挤,好几次幼弱的身体被大人们挤得悬在空中。常常在众目睽睽之下,灰溜溜敲开教室的门,走到最后一排坐下。放学,我得等妈妈下班接我,她就在附近的陕西北路、威海路上班,但学校三四点就放了,她有时要加班到五六点。班主任、教语文的张老师和教数学的蔡老师对我特别照顾,把我留在办公室——对面的民居,做作业,直到妈妈来接我,她们才下班。她们都劝我妈妈:这样没意思,耽误孩子学习。其实也没怎么太耽误,前十名还是有的,转学时大概是第三吧。前面落后些,是因为黄浦的幼儿园没教过拼音,而多数是静安生源的同学早学过了。蔡老师还来过我家,很热心地想帮我家“调房子”到静安一处石库门,但对方家里丈夫突然得了急病,遂作罢。
就这么在66路、18路、15路、20路等等公交车上,折腾了一年,妈妈终于认命,不要我接受“上只角”的教育了,同意我在闸北读书。但转学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吗?本质上,还是计划经济时代,什么都要“开后门”。“开后门”那个词,就是那年头流行起来的。
那年头,上海的轻工业业绩很好,热卖全国,爸爸在市级主管单位当个小干部,路子多,就托了人,辗转到闸北区某中心小学(下简称“某中心”)。转学前那个暑假,爸爸带我去参加特别组织的摸底考,好像就我一个人考,但有好几个老头看着我做卷子,连十二生肖都考,幸亏我幼儿园有条小手绢上印全了,背得烂熟。
第一次去某中心,是1987年暑假快结束时的返校活动。这是一所位于中兴路、宝通路的学校,虽然闸北是工业区加贫民窟,向为沪人鄙视,但某中心附近有基督教闸北堂(我幼儿园时,身为党员的爸爸带后来归心佛教的我参加过这里的圣诞弥撒)和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旧址,陈云同志战斗过的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也在附近,算是不学之地的人文荟萃吧。
返校,我谁都不认识,班主任把我介绍给全班,然后把其他人介绍给全班。原来我不是唯一转来的。返校的目的呢,是检查暑假作业和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是……是……是……是捡牙膏皮!!!谁捡得多,谁就是好苗苗。我回家就问妈妈:那些同学就不读书,不玩吗?为什么要捡牙膏皮呀?妈妈也不大懂。那年头,牙膏真是精贵的东西啊,牙膏皮何其难得?我初中第一次向女生表白,送的就是国内稀罕的Golgate牙膏。果然,不久发现了有同学为了多得牙膏皮,挤光了家里的牙膏,被大人痛骂,还告诉了老师。
班主任W老师呢,也是个美女。和董老师不同,她发型有点洋气,我甚至中学的春梦里都出现过她……数学沈老师则是个老太太了。我对W老师最初的印象还好。她粉笔字写得很工整,上课也挺生动,像电视里的燕子姐姐陈燕华。但不知为何,她对我有顽固的歧视,总是把我放学后留下来“练坐”。
“练坐”也就是暴力程度轻些的体罚。每天放学前,W老师会静静扫视一遍全班,报出须练坐者的名字。必须腰挺直,双手放于背后,至少这么坐一节课。罚“练坐”的理由很单一:上课捣乱。我是捣乱了,但我很快识相了,上课不乱说乱动了,怎么还要我“练坐”呢?老师的理由是:同学,你病得不轻,需要巩固巩固疗效。好吧。
很多年后,大概是我读大学了吧,有一天突然对妈妈说:“想我当年读书这么差,也能进复旦啊?人生真是太无常了。”妈妈问我怎么差了。我说高中考试都不及格啊,小学常常挨罚“练坐”啊。谁知她突然蹦出一句:“那个W老师?你知道她为什么要你天天‘练坐’吗?”“不知道啊!”“还不是为了你爸爸的票子!”我没有小伙伴,当时独自惊呆了。
原来,老师不是要我巩固,是全校有很多老师要洗衣机票子,要修洗衣机。洗衣机那时是紧俏的商品,凭票供应,而我爸爸调到洗衣机总厂了,为保障我在学校卑微的存在,他竟然向老师们另类的威胁服软了。
果然,后来不怎么叫我“练坐”,因为要多少票子,爸爸扯张白纸,写几个字就行。家里洗衣机坏了?没事,爸爸一个电话,第二天工人师傅就上门服务,包你修好,而且分文不取。不是不取,是不敢去,回头爸爸给。你取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钱,回头工程师就把我的灵魂给修理了,怎么得了?
但爸爸手上这点特权根本没有为我在校内地位的提升起到任何正面作用,有更大特权的家长还有好好几位。那时,谁家父是厂长,谁家母是书记,所有同学都知道。每到教师节、过年,教师办公室门庭若市。人家长都去,你家长能不去吗?可你家长要想只送本挂历,就免了吧,太寒碜,丢不起那人啊!妈妈就这样被“请”出过办公室,下详。
就在我自感适应某中心的节奏之际,W老师约见我妈妈,沉痛宣告:“你儿子太差了,从静安来我们闸北,学习完全跟不上,可能要留级或者退学,你们家长要做好思想准备。”后来妈妈告诉我,她回来路上就哭了。而我至今莫名其妙,我虽然没教养,不读书,可成绩真的不是最差的,一直保持中不溜秋,怎么就要闹到读不下去的份儿上了呢?实在是气场不合吧。
W老师治下,我特别爱打架,还吃过两次苦头。一次是后来发生的,我下课和小伙伴们去工地打架,我一颗石子飞出去——当时单田芳正说《白眉大侠徐良》——打破了我同学、教导主任之侄子的脑门,受力点就在右眼和右侧太阳穴之间。血流如注,我当时吓蒙了,以为会枪毙,结果没有。赔钱,人家不要,只收了两袋奶粉。高风亮节!这次呢,我认罪伏法,一人做事一人当。但另一次,早前发生的,是一群男生追打另一个学生,我是冤枉的。被追打的叫王菲,三年级去了香港,可惜是男的。王菲近视眼,慌不择路,一头撞在楼梯扶手上,撞破了脑袋。W老师无端认定我是主谋。呸!我当时跑在队尾,那些跑在前头的,她倒不问一词。后来,W老师把儿子带来班里玩,在我身边不小心摔倒,又怪到我头上。再后来,才貌双全的W老师高升,执掌其他学校去了。
我前面提到一位沈老师,不是没道理的。沈老师和其他好多老师不同的地方,在于她很少收礼。即便收礼,也一定还礼,至少等值。很真诚,甚至送到我家里来。爸妈后来也就不给她送礼了。我对某中心几乎没有任何好印象,除了她。她还是尊重学生和家长的,没有因为当了老师,拿起教鞭,就自命为特权阶级。可惜,这样的人,当时就很难得。我从教数年,每次学生来送礼,我都会想起忠厚勤勉的沈老师。
气场还不合的一处,是伙食。在南京路时,学校太小,没法开食堂,各自解决伙食。很多同学离家近,就回家吃,我太远了,也不能去妈妈单位吃——社会主义的企业有严格的规定吧——妈妈就托了关系,安排我到近水楼台的梅龙镇饭店吃。今天,梅龙镇和上海其他所有老字号一样,都衰败得不成样子(杏花楼除外,杏花有很多黄牛拉出的肥料,所以一花独秀,常开不败),可当年的梅龙镇是南京西路最有名的饭庄,生意极好,也做起了社会公益:给附近学生提供午餐搭伙。我在微博曾回忆过,午餐基本不错,菜都是大厨掌勺,有订酒水的吃鱼中段,我们就吃鱼头或鱼尾巴,米饭敞开供应,但安排我们吃饭的地下一层常常停电,也不止是那里,整条南京西路都有事没事就停电,商店点白蜡烛营业。有次吃鱼头,我不吃,服务员逼着我吃,否则不让我去上课,我咬了几口就抱着门口的石狮子狂吐。我此后再也没碰过鱼头。就是这样的美馔佳肴,养刁了我的胃口,吃不惯某中心食堂供应的午饭。
某中心的午饭,猪食都不如。我如今贪吃,就是因为那年头很难吃,不敢吃,吃不饱。奇怪的是,同学们个个狼吞虎咽,扫荡净尽。收饭盒的师傅每次看到我一口不动地还回去,就瞪我白眼,骂我,说我不珍惜粮食,不让我去上课。惊动了班主任,她就真的拿着饭盒,叫我去办公室,把饭盒放在暖气炉上,让我吃完了再去上课。可是,我本来就不爱上课啊,这样不是挺好嘛。最后,没辙,又叫我妈妈来学校。那天很多家长都来学校看孩子吃午饭,食堂烧得特别好,我第一次吃完某中心的午饭。后来,妈妈又突击考察了一次,看到我平时的午饭,回去跟爸爸说:“真的质量很差。”她当时是党的基层干部,现在是退了休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她什么都会,就不会说谎。差到什么程度?每一盒饭,都能挑出不下十条虫。饭盒是我们搭伙的人,每人交一个。我交了个新的不锈钢的。后来可以退伙了,我就第一时间去领回饭盒,领回个旧的铝的。
领回饭盒的那天,放学,刚出校门,见一大群哥哥姐姐模样的人手拉手,慢悠悠从门口的中兴路走过,还有人举着横幅,上书“同济大学”。这是我三年级的事。那阵子,上海群众活动也多,公交瘫痪,爸妈都没法坐车去上班。而我天天盼望学校散伙的中国梦,到底没有实现。只是老师问家长要东西的风气消停了些。大学看BBS,看FTP,才晓得首都很多细节,不胜唏嘘。多事之夏一过,一切定性,学校组织我们停课去生物实验室看CCAV播放的光荣镜头。回忆起来,整个民族就是从那时起,破釜沉舟地一切朝钱看了。我们也换了老师,班主任、语文老师是H1,数学老师是H2。
据很多家长说,H2是英俊潇洒极了,反正我对男色不敏感。但H2对我们很凶,上课经常骂学生“脑子坏掉了”、“恶戆——又恶又戆”、“黄鱼脑子”、“寿棺材”,我跟着他,迅速掌握了上海方言的多数俚语。这样的好老师,当然晋升也很快,后来还上过电视教课。他和有些同学住在一个小区里,同学做不出作业就去他家问。可惜好景不长,据传师母怒了。有回上面来调查学生对他的满意度,很多同学就写了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坐我后面的陆同学,写了他“上课不讲普通话”。调查的同志回去了,H2来了解情况。就有小人把陆同学写的内容,当场揭发了出来,惹得H2顿时变脸。这个揭发同伴以邀上宠的小人不是别人,就是我。所以,我的无耻,是有历史根基的。但,我,忏,悔,了。
H1老师一脸严肃,讲课认真,照片前几年上过本市大报。但处理问题比较僵化。当时,刚被撤去小队长的我和霸占学习委员一职的董同学是班里成绩最好的,为了女人也常常争风吃醋,被和我关系很要好的班长陈同学揭发——看,这股风气不是我一个人在玩啊——写了篇日记,大意是希望全班在他的治理下能保持和谐、稳定、繁荣,不希望我和董这样龙争虎斗下去。H1看了日记(喂,干吗要给老师看啊?),大怒,把我叫去,问了我一句话,字字印在我脑中:“实际情况和他写的有出入吗?”可是,我那么小,不懂什么叫“出入”啊!我糊里糊涂,答了个“没有”。H1立马叫我回教室去,从此对我再没好脸色,我开班会抖脚都要挨恶狠狠的骂。董同学一样没好日子过,但他毕竟是有官位的人,瘦死的骆驼。去年,在人人网上认识个学弟,他说,H1老师居然在课上批评他们不给她买KFC吃,听来不可思议。我毕业后还和同学去H1老师家玩了两次,因为离着很近。老师让我和他儿子打游戏。但妈妈知道了,不大开心,估计是因为送挂历吃了闭门羹。女人啊……前几年,有个苏北的朋友租了房子,在我家附近,叫我去玩。跑去一看,嚄,这不是H1老师家嘛!
这段历史斗争时期内,还发生了体育老师被炒鱿鱼的事,使得广大老师对职业操守问题有所警觉。那位老师,好像姓张,很喜欢打学生,比“练坐”痛快多了。我算耳光吃得少的,吃过一个,至今耳鸣不歇。其他同学,大概是回去的脸型像是首尔整过了,给家长联名告到学校,丢了饭碗。我是家长,我也气啊,平时你们要什么,我们给什么,不就是为了对我孩子好点吗?还打人,杜月笙也要灭了你啊!
那时,师范中专生还要来实习。有阵子,突然老师就消失了一样,全给师范生接管。我们班来了俩,胖的那个姓毛,瘦的那个姓章。姓章的很喜欢坐我后面的女同学,有一次我和邻桌男生打架,推翻了课桌,压到了这位女同学的脚面,女同学痛苦地大哭,章老师震怒,把我关进学校临时搭建的小黑屋,不让我回家。毛老师给我说了好几次情,他才傍晚放我回去。听说后来他们都没有做教师这一行,毛可惜了。
五年级,要毕业升初中了。送礼风又刮起来。也不知怎么的,同学间传得很快,说大队长家是邮电局的,给校长送了正版猴票,等等等等。为什么要送礼呢?当时有全市统一的升学考试啊。没错,可那年,我们班走运,教委在谢丽娟同志领导下,搞“小学全班整体直升”试验,选到我们。我们只有两个名额,一个去上外附中,一个去闸北当时唯一的市重点市北中学。名额给谁呢?最后,考下来,也巧了。大队长、班长、我三个人非但总分一样,是全校最高的285分(满分300),连语数外各门分数都一样。大队长去了上外附中,班长去了市北中学,我则“整体直升”去一家附近弄堂里的普通中学也。六年后,从上海中学毕业,再联系老同学,得知大队长去了上外,班长去了上大,想想我进复旦,也不算太差,心气便平复了些。
至于校长,收没收猴票,我当然不好说。但过了几年,竟因为经济问题,锒铛入狱,倒是同学甚至老师都在传的。我也没见她进提篮桥,也不好说什么。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舅舅家楼下,她当时正指挥一辆车停进车位,我和她一起坐了一段电梯。她当然认我不出。
本文纯属回忆,虽然我记性极好,但未必全部准确真实,权当教师节有个教书的说了番梦话,姑妄听之。
总的说来,从我个人的经历可以看出,教师队伍和社会上其他职业一样,有好有坏,不必神圣化。神圣化,是因为有人发不起好教师的工资,提不高好教师的地位,如此而已。读书人向往的“师道”是很高尚的,可惜人间难寻。这番道理,我很早领悟,所以从教之初,我就不接受“师”字。别人称我是老师,除在课堂外,一概谢绝,只称自己是“某某大学职工”。这不是我装逼,只是我对“师道”还寄托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而已。这里回忆的是我初中前的一些教育经历,一些人,一些事。我也是坐三望四的人了,杂事渐多,记忆衰退,早点写下,以免忘记。将来有谁研究改革开放后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问题,希望能对他或她有些零零碎碎的时代背景上的参考价值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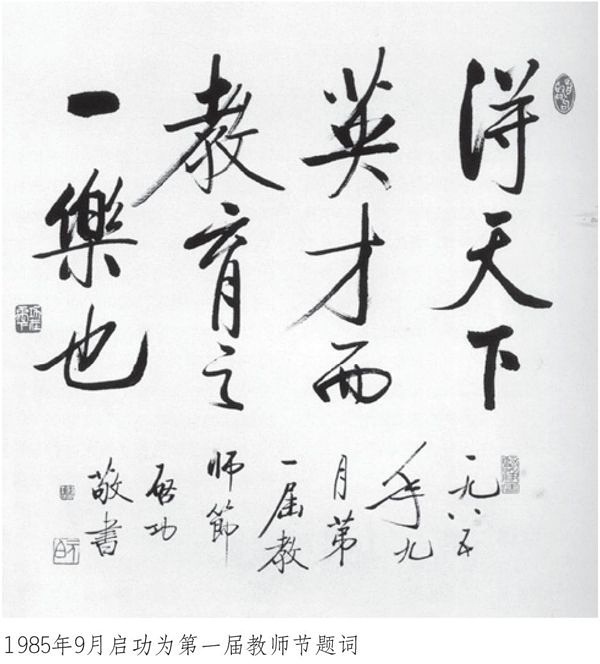

 RSS Feed
RSS F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