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4-27 17:25:33
男人,就是有所谓家累,否则都可以活得潇洒些吧。
我本意杯葛“世博”。奈何高堂年迈,恐他日有欲养不在之憾,恰好组织上寄来两张“测压”票(大概是看我质量大,贡献的压力也大),称是答谢对翻译工作的支持,就硬着头皮,带着妈妈去了。
为了避开人流高峰,下午2点出发,坐了世博20路。一辆崭新的公交,加司机共3人。临到终点,才上来一个长得像“海宝”GF的女孩。司机大概是心疼车太新了,开得很慢。于是,我们下只角居民饱览了新外滩一路风光。加上我眼神特好,连滨江大道某小偷用的是哪几根手指头摸的游客手机都瞧得如黄浦江水般一清二楚。这2块钱车票很值。
下车是3号入口,只需步行1km就到安检。安检有两个口,一个给志愿者走,人山人海。一个给我们游客走,没人的,但过道设置成了一道鲁菜的花式:“九转大肠”,5米左右的位移,实际要行100米多,看看走在前面的大爷真搞笑,跟戏台上跑圆场一样。组委会啊组委会,我的心明明白白,这是让我们都不能忘记伤了脚的跨栏英雄刘小翔。
安检真是严格,我出入境都没享受过的待遇,这回都用上了。检查我的是个女的,一手拿探雷器样物,猛扫我全身;一手持“翻天印”,上篆类似“猪肉合格”字样。在这几分钟里,我闭眼冥想:如果我是恐怖分子,该如何利用漏洞,顺利通过安检。还没想出结论,就被搜出了违禁物品:唇膏和滴眼液。一枚中原男立刻上来,说:“不许带进去!”我说:“旁友,狄额么事老巨额,好伐!”“允许你当场涂掉,立刻滴完!”我没辙了。中原男的顶头上司一旁看到,使劲给中原男递眼色。遂放行。
浦西园区据说人少些,身临其境,对于场馆种类,基本果是一目了然。我总结起来,就是场馆分两种:
(甲)有人排队的场馆
(乙)没人排队的场馆
甲种的特点是必须排队,绕场受罪,排到你时,明日再会。
乙种的特点是不用排队,外观免费,要想进入,明日再会。
随便走走,没啥花头,在船舶馆的大缆绳上坐了会儿,发现这里是江南造船厂车间改造的,全是生钢硬铁,果然上海办“世博”有坚强的物质基础。等来了做志愿者的“大黄丸”同学,他送我们去了渡口,就回家了。他做一休二,即一不做二不休:上午8点上岗,24点下班。1米9的大个儿,老说这里吃不饱饭,或者说,是吃不起饭。
一路无话,到了浦东,气氛迥异。喇叭里不停地重复:“德国馆排队人数较多,已达3小时”(这话语法好赞!)过一会儿成了:“德国馆吃不消了,已经闭馆。”又过一会儿:“德国馆照顾参观者情绪,开到今晚10点钟,大家现在别去。”然后就是“泰国馆……”,打的都是一个套路:“迷踪拳”。其实,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很多馆不是提早打烊,就是压根没好。我国游客普遍崇洋媚外情绪高涨,总得去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馆看看人家生活如何“水深火热”吧。法西斯看不成,人妖还不给看啦?!
我们一个年老,一个体弱,只好走马观花。走着走着,发现马腿要断了,就坐下来歇歇,啃啃面包——自己带的,啃得起。到底是中国人办的“世博会”,花坛啊,水池啊,时不时就给来点儿中国特色:垃圾。
非洲联合馆是第一个接纳我们的馆。有几个黑人在卖力唱歌,韵律远听像苏州弹词。还有几个黑人在各国服务台坐着,供游人拍照借用:其中一位,居然能在我观察他的五分钟里,纹丝不动,眼皮都不眨一下。妈妈说:“这有什么奇怪的,伊是塑料组额呀!”出馆时,我感叹道:“还是第三世界人民靠得住,还是黑人兄弟靠得住!”
智利馆和芬兰馆人流涌动得很快,我们随喜了。这两个馆的好处就是像毛主席纪念堂,进去,一直走,就出来了。而它们和纪念堂的重要区别在于:它们连个可看的死人都没有。死人没看到,但在智利馆,我和一南美大帅哥在印加裸体女像下畅谈了几分钟艺术:
I: This is the symbol of your culture?
He: Oh, no. It is just a statue, a welcome statue.
I: Great! It's a nude woman, I see, with a fruit basket on top of her head.
He: Oh, yes.
I: Women in your country prefer to be nude in public?
He: Oh, hopefully.
在芬兰馆,看到了吵架——我最爱围观的街头娱乐项目。两个中年男子(当然,都是阿拉上海宁)处于殴斗的边缘(正因为都是上海宁,按周立波第二定律,处于殴斗边缘,即与殴斗绝缘),其中一个被老婆拉走了,另一个大概是离婚户头,没人拉,落得个原地撒泼打滚,一边嚷嚷着:“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想上去问:“旁友,日币有伐?”被妈妈拉走了。可是那男子不依不饶。一位芬兰工作人员小姐很迷惑,以为工作没做到位。
She: What is that gentleman shouting about?
I: He’s just trying to say “Long live the friendship between Finland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the highest volume of voice. Believe me. He'd have been gentler.
美国人是会赚钱的,全馆只开放餐厅和商店,可见此次经济危机之深刻。看了看,基本都是看得起F1的人才买得起的东东。乃落荒而逃。
要说大国馆,除了我们抄袭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加拿大馆的“东方之鼎”外,还就数俄罗斯的气派,白黑红金,恰是我最喜爱的色彩组合,而磅礴的气势中,点缀着精雕细琢的花纹,让我联想起外冷内热的西伯利亚和外热内冷的克格勃。油漆没刷完,也不开。
欧风美雨过后,是大洋洲。这是唯一一个所有国家馆都关了的洲。新西兰馆造的假树比真的还真,肯定背后是义乌工程师在撑腰。工作人员有华裔,和众游客有说有笑,沟通便利。澳大利亚馆则留了零食小卖部开着,门口还有白人歌手深情弹唱。所幸听歌和现金消费零食不一定非要发生经济上的必然关系。
南极洲没参展,所有就剩下亚洲了。要说建筑花头多,特征强,还就属我们亚洲人。远望泰国馆,就知道是泰国馆,哪怕不见个人妖。但见到个妖人,老道模样,躺在馆口地板上,围了六七个保安。但听“老道”嘴里念念有词:“阿拉排了两只多钟头额队,侬刚闭馆就闭馆啦?!老夫今日拼将一死,也要进去看个究竟!”保安让他这话吓得要命,每人掏出一台对讲机,跟上级汇报。与此同时,“老道”作三聚氰胺中毒剧烈抽搐状。几个泰国人在馆内,陪着我笑眼旁观。
越南好像没有独立的展馆,大概忙于“改革开放”(按:细心读者指出,是有的。恕我野外定向能力太拙。)。柬埔寨有,打的是吴哥的招幌,门口是锡兰狮子、象、神猴,当然还有佛的舞者:aspara们。它倒是太太平平闭馆了。门没关,探头看看:嚄,就是家工艺品商店!
这次的主题馆是关于城市的,从地图上看,建筑规模最大。入口又是“九转大肠阵”。但这里保安开小差去了,于是猴精的大爷大妈们顿时放下骨骼僵硬的架子,爬上钻下,既活动了经络,又节省了脚力。待到保安发现,上前劝阻,他们祭出“老年卡”,便也通行无阻,相安无事。进了城市生命馆,走过几排大管道(算是城市的是大肠吧),看了一场小电影,三步五步,就出来了。其他部分呢?哦,楼上的“绍兴饭店”欢迎你。
最后是中国馆,只有省市区馆还允许游人进入。省市区馆又分成两派:剑宗的GDP派和气宗的UNESCOW派。前者以广东为极致,给人的印象是这个省都姓“王”——名“老吉”,布展的珠江两岸宽幅照片里,赫然一家工行的招牌写着“ICBCBC”。明白了,这是段对话。工行:“爱存不存!”客户:“不存!”。到底是黄飞鸿、方世玉的同乡,有骨气!后者以陕西为大观,照例拿杨贵妃洗澡说事儿,吹拉弹唱,载歌载舞,好不热闹,门口则矗立一座“雷”神组合雕塑:“海宝”携手兵马俑。仿佛听到兵马俑对“海宝”说那句CCAV老版《西游记》里那句著名的台词:“师傅,快随我去,快随我去吧!”一边艺人们在剪纸作画。有游客看着大红的剪纸喜气洋洋,想买。艺人说:“领导说了,不卖。你实在要是喜欢,给十块钱吧。别让人瞧见。”他一抬头,发现我在“窃听”,严肃地用手里的笔指指桌上一本本子:“小伙子,给留个言吧。”我要是留了言,妈妈必又要说我惹是生非,便赶紧退出了交易现场。
最让我难忘的还得数湖南馆。门庭清幽,站满了迎宾的礼仪小姐,个个笑容神似天҉安҉门҉上的太祖遗像。我刚要悠然踱入,保安一只胳膊肘就撞向了我的胸口:“闲人让开!”“怎么?闭馆了?”他都不屑搭理我,眼睛直盯着前方。这时,礼仪小姐的面部表情由拈花微笑爆发成冰岛火山喷发:“领导来啦!”啊呀,我一介草民,冲撞了领导车驾,那还了得!赶快退避2米。果然,一彪男女快步走近,簇拥着一位中年大妈。大妈不曾露脸于CCAV 1著名长篇无休止连续剧《新闻联播》,更不是SMG追踪的那几位,因此断定为湖南母官——父官八成忙着鞠躬鱼肉,尽瘁觥筹,无暇莅临指导。再说那班小姐,突然有一个,三步并作两,上去就抱住领导的胳膊:“我也是株洲人啊!!!”领导:“哇塞!这么巧!”一众人马,随这一唱一和,进了馆内,皆大欢喜。晦气,独我不是株洲人!哎,可我姓朱啊,是不是也能跟领导攀上个关系?再用阿Q的逻辑想想,当年我们朱家坐拥江山,那位领导要来抱我胳膊,怕是还没走到近前,已叫御林军拖出去廷杖了吧。NND,湖南馆,老子不进去了!(但临走路过,忍不住,还是进去了。怪不得我朱家守不住江山啊……人贱!)
上海馆和浙江馆要排队,我就不凑那热闹了。其他省市区则一路兜完,总体感觉平平,亮点只有云贵:也是因建筑风俗一花独秀。如果要我提改进的意见,那就是“党的领导”不够突出,资本主义和“四旧”的戏份都重过头了——山东馆居然抬出个孔老二的塑像来,脑袋上还没顶着“海宝”!
还想出去转转,保安说整个园区要关闭了。便催动将断未断的双腿回家。中国馆左边有港澳两馆,右边有台湾馆(这个老右派!),只能远远开几眼。澳门馆的兔子灯造型很有趣。第一眼看到,我就想:组撒不做成其他造型呢?譬如手信。再一想,兔子灯恐有深意存焉:
(甲)由活转死(兔型)
(乙)一捅就破(纸做)
(丙)听任摆布(绳牵)
(丁)心里明白(灯亮)
(戊)弥天大X(“宝”鼎之“盖”罩在“兔”子“头”上)
(己)……
天呐,不能再往下想了,再想这澳门馆就该拆咯。
回首望宝鼎,中心念天朝。思如涌泉,赋诗一篇:
上海市民真欢喜
世博盛会邀请你
参观排队要牢记
千万耐心沉住气
有些需要预约机
多数单靠双腿立
但愿保安不在意
上窜下跳得便宜
烧钱建议进园吃
不烧自带也可以
吃完垃圾且随地
扔了也有人捡起
带干无妨莫带湿
带湿就要惹怀疑
恐怖实非好主义
共产才是大真理
浦江两岸多壮丽
对此怎能不感泣
伦敦初会犹睡狮
今朝东方啼雄鸡
拜托来福拜习题
(i.e.,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来福习题皆奇迹
世纪巨变谁功绩
D的政策雅客稀
男人,就是有所谓家累,否则都可以活得潇洒些吧。
我本意杯葛“世博”。奈何高堂年迈,恐他日有欲养不在之憾,恰好组织上寄来两张“测压”票(大概是看我质量大,贡献的压力也大),称是答谢对翻译工作的支持,就硬着头皮,带着妈妈去了。
为了避开人流高峰,下午2点出发,坐了世博20路。一辆崭新的公交,加司机共3人。临到终点,才上来一个长得像“海宝”GF的女孩。司机大概是心疼车太新了,开得很慢。于是,我们下只角居民饱览了新外滩一路风光。加上我眼神特好,连滨江大道某小偷用的是哪几根手指头摸的游客手机都瞧得如黄浦江水般一清二楚。这2块钱车票很值。
下车是3号入口,只需步行1km就到安检。安检有两个口,一个给志愿者走,人山人海。一个给我们游客走,没人的,但过道设置成了一道鲁菜的花式:“九转大肠”,5米左右的位移,实际要行100米多,看看走在前面的大爷真搞笑,跟戏台上跑圆场一样。组委会啊组委会,我的心明明白白,这是让我们都不能忘记伤了脚的跨栏英雄刘小翔。
安检真是严格,我出入境都没享受过的待遇,这回都用上了。检查我的是个女的,一手拿探雷器样物,猛扫我全身;一手持“翻天印”,上篆类似“猪肉合格”字样。在这几分钟里,我闭眼冥想:如果我是恐怖分子,该如何利用漏洞,顺利通过安检。还没想出结论,就被搜出了违禁物品:唇膏和滴眼液。一枚中原男立刻上来,说:“不许带进去!”我说:“旁友,狄额么事老巨额,好伐!”“允许你当场涂掉,立刻滴完!”我没辙了。中原男的顶头上司一旁看到,使劲给中原男递眼色。遂放行。
浦西园区据说人少些,身临其境,对于场馆种类,基本果是一目了然。我总结起来,就是场馆分两种:
(甲)有人排队的场馆
(乙)没人排队的场馆
甲种的特点是必须排队,绕场受罪,排到你时,明日再会。
乙种的特点是不用排队,外观免费,要想进入,明日再会。
随便走走,没啥花头,在船舶馆的大缆绳上坐了会儿,发现这里是江南造船厂车间改造的,全是生钢硬铁,果然上海办“世博”有坚强的物质基础。等来了做志愿者的“大黄丸”同学,他送我们去了渡口,就回家了。他做一休二,即一不做二不休:上午8点上岗,24点下班。1米9的大个儿,老说这里吃不饱饭,或者说,是吃不起饭。
一路无话,到了浦东,气氛迥异。喇叭里不停地重复:“德国馆排队人数较多,已达3小时”(这话语法好赞!)过一会儿成了:“德国馆吃不消了,已经闭馆。”又过一会儿:“德国馆照顾参观者情绪,开到今晚10点钟,大家现在别去。”然后就是“泰国馆……”,打的都是一个套路:“迷踪拳”。其实,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很多馆不是提早打烊,就是压根没好。我国游客普遍崇洋媚外情绪高涨,总得去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馆看看人家生活如何“水深火热”吧。法西斯看不成,人妖还不给看啦?!
我们一个年老,一个体弱,只好走马观花。走着走着,发现马腿要断了,就坐下来歇歇,啃啃面包——自己带的,啃得起。到底是中国人办的“世博会”,花坛啊,水池啊,时不时就给来点儿中国特色:垃圾。
非洲联合馆是第一个接纳我们的馆。有几个黑人在卖力唱歌,韵律远听像苏州弹词。还有几个黑人在各国服务台坐着,供游人拍照借用:其中一位,居然能在我观察他的五分钟里,纹丝不动,眼皮都不眨一下。妈妈说:“这有什么奇怪的,伊是塑料组额呀!”出馆时,我感叹道:“还是第三世界人民靠得住,还是黑人兄弟靠得住!”
智利馆和芬兰馆人流涌动得很快,我们随喜了。这两个馆的好处就是像毛主席纪念堂,进去,一直走,就出来了。而它们和纪念堂的重要区别在于:它们连个可看的死人都没有。死人没看到,但在智利馆,我和一南美大帅哥在印加裸体女像下畅谈了几分钟艺术:
I: This is the symbol of your culture?
He: Oh, no. It is just a statue, a welcome statue.
I: Great! It's a nude woman, I see, with a fruit basket on top of her head.
He: Oh, yes.
I: Women in your country prefer to be nude in public?
He: Oh, hopefully.
在芬兰馆,看到了吵架——我最爱围观的街头娱乐项目。两个中年男子(当然,都是阿拉上海宁)处于殴斗的边缘(正因为都是上海宁,按周立波第二定律,处于殴斗边缘,即与殴斗绝缘),其中一个被老婆拉走了,另一个大概是离婚户头,没人拉,落得个原地撒泼打滚,一边嚷嚷着:“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想上去问:“旁友,日币有伐?”被妈妈拉走了。可是那男子不依不饶。一位芬兰工作人员小姐很迷惑,以为工作没做到位。
She: What is that gentleman shouting about?
I: He’s just trying to say “Long live the friendship between Finland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the highest volume of voice. Believe me. He'd have been gentler.
美国人是会赚钱的,全馆只开放餐厅和商店,可见此次经济危机之深刻。看了看,基本都是看得起F1的人才买得起的东东。乃落荒而逃。
要说大国馆,除了我们抄袭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加拿大馆的“东方之鼎”外,还就数俄罗斯的气派,白黑红金,恰是我最喜爱的色彩组合,而磅礴的气势中,点缀着精雕细琢的花纹,让我联想起外冷内热的西伯利亚和外热内冷的克格勃。油漆没刷完,也不开。
欧风美雨过后,是大洋洲。这是唯一一个所有国家馆都关了的洲。新西兰馆造的假树比真的还真,肯定背后是义乌工程师在撑腰。工作人员有华裔,和众游客有说有笑,沟通便利。澳大利亚馆则留了零食小卖部开着,门口还有白人歌手深情弹唱。所幸听歌和现金消费零食不一定非要发生经济上的必然关系。
南极洲没参展,所有就剩下亚洲了。要说建筑花头多,特征强,还就属我们亚洲人。远望泰国馆,就知道是泰国馆,哪怕不见个人妖。但见到个妖人,老道模样,躺在馆口地板上,围了六七个保安。但听“老道”嘴里念念有词:“阿拉排了两只多钟头额队,侬刚闭馆就闭馆啦?!老夫今日拼将一死,也要进去看个究竟!”保安让他这话吓得要命,每人掏出一台对讲机,跟上级汇报。与此同时,“老道”作三聚氰胺中毒剧烈抽搐状。几个泰国人在馆内,陪着我笑眼旁观。
越南好像没有独立的展馆,大概忙于“改革开放”(按:细心读者指出,是有的。恕我野外定向能力太拙。)。柬埔寨有,打的是吴哥的招幌,门口是锡兰狮子、象、神猴,当然还有佛的舞者:aspara们。它倒是太太平平闭馆了。门没关,探头看看:嚄,就是家工艺品商店!
这次的主题馆是关于城市的,从地图上看,建筑规模最大。入口又是“九转大肠阵”。但这里保安开小差去了,于是猴精的大爷大妈们顿时放下骨骼僵硬的架子,爬上钻下,既活动了经络,又节省了脚力。待到保安发现,上前劝阻,他们祭出“老年卡”,便也通行无阻,相安无事。进了城市生命馆,走过几排大管道(算是城市的是大肠吧),看了一场小电影,三步五步,就出来了。其他部分呢?哦,楼上的“绍兴饭店”欢迎你。
最后是中国馆,只有省市区馆还允许游人进入。省市区馆又分成两派:剑宗的GDP派和气宗的UNESCOW派。前者以广东为极致,给人的印象是这个省都姓“王”——名“老吉”,布展的珠江两岸宽幅照片里,赫然一家工行的招牌写着“ICBCBC”。明白了,这是段对话。工行:“爱存不存!”客户:“不存!”。到底是黄飞鸿、方世玉的同乡,有骨气!后者以陕西为大观,照例拿杨贵妃洗澡说事儿,吹拉弹唱,载歌载舞,好不热闹,门口则矗立一座“雷”神组合雕塑:“海宝”携手兵马俑。仿佛听到兵马俑对“海宝”说那句CCAV老版《西游记》里那句著名的台词:“师傅,快随我去,快随我去吧!”一边艺人们在剪纸作画。有游客看着大红的剪纸喜气洋洋,想买。艺人说:“领导说了,不卖。你实在要是喜欢,给十块钱吧。别让人瞧见。”他一抬头,发现我在“窃听”,严肃地用手里的笔指指桌上一本本子:“小伙子,给留个言吧。”我要是留了言,妈妈必又要说我惹是生非,便赶紧退出了交易现场。
最让我难忘的还得数湖南馆。门庭清幽,站满了迎宾的礼仪小姐,个个笑容神似天҉安҉门҉上的太祖遗像。我刚要悠然踱入,保安一只胳膊肘就撞向了我的胸口:“闲人让开!”“怎么?闭馆了?”他都不屑搭理我,眼睛直盯着前方。这时,礼仪小姐的面部表情由拈花微笑爆发成冰岛火山喷发:“领导来啦!”啊呀,我一介草民,冲撞了领导车驾,那还了得!赶快退避2米。果然,一彪男女快步走近,簇拥着一位中年大妈。大妈不曾露脸于CCAV 1著名长篇无休止连续剧《新闻联播》,更不是SMG追踪的那几位,因此断定为湖南母官——父官八成忙着鞠躬鱼肉,尽瘁觥筹,无暇莅临指导。再说那班小姐,突然有一个,三步并作两,上去就抱住领导的胳膊:“我也是株洲人啊!!!”领导:“哇塞!这么巧!”一众人马,随这一唱一和,进了馆内,皆大欢喜。晦气,独我不是株洲人!哎,可我姓朱啊,是不是也能跟领导攀上个关系?再用阿Q的逻辑想想,当年我们朱家坐拥江山,那位领导要来抱我胳膊,怕是还没走到近前,已叫御林军拖出去廷杖了吧。NND,湖南馆,老子不进去了!(但临走路过,忍不住,还是进去了。怪不得我朱家守不住江山啊……人贱!)
上海馆和浙江馆要排队,我就不凑那热闹了。其他省市区则一路兜完,总体感觉平平,亮点只有云贵:也是因建筑风俗一花独秀。如果要我提改进的意见,那就是“党的领导”不够突出,资本主义和“四旧”的戏份都重过头了——山东馆居然抬出个孔老二的塑像来,脑袋上还没顶着“海宝”!
还想出去转转,保安说整个园区要关闭了。便催动将断未断的双腿回家。中国馆左边有港澳两馆,右边有台湾馆(这个老右派!),只能远远开几眼。澳门馆的兔子灯造型很有趣。第一眼看到,我就想:组撒不做成其他造型呢?譬如手信。再一想,兔子灯恐有深意存焉:
(甲)由活转死(兔型)
(乙)一捅就破(纸做)
(丙)听任摆布(绳牵)
(丁)心里明白(灯亮)
(戊)弥天大X(“宝”鼎之“盖”罩在“兔”子“头”上)
(己)……
天呐,不能再往下想了,再想这澳门馆就该拆咯。
回首望宝鼎,中心念天朝。思如涌泉,赋诗一篇:
上海市民真欢喜
世博盛会邀请你
参观排队要牢记
千万耐心沉住气
有些需要预约机
多数单靠双腿立
但愿保安不在意
上窜下跳得便宜
烧钱建议进园吃
不烧自带也可以
吃完垃圾且随地
扔了也有人捡起
带干无妨莫带湿
带湿就要惹怀疑
恐怖实非好主义
共产才是大真理
浦江两岸多壮丽
对此怎能不感泣
伦敦初会犹睡狮
今朝东方啼雄鸡
拜托来福拜习题
(i.e.,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来福习题皆奇迹
世纪巨变谁功绩
D的政策雅客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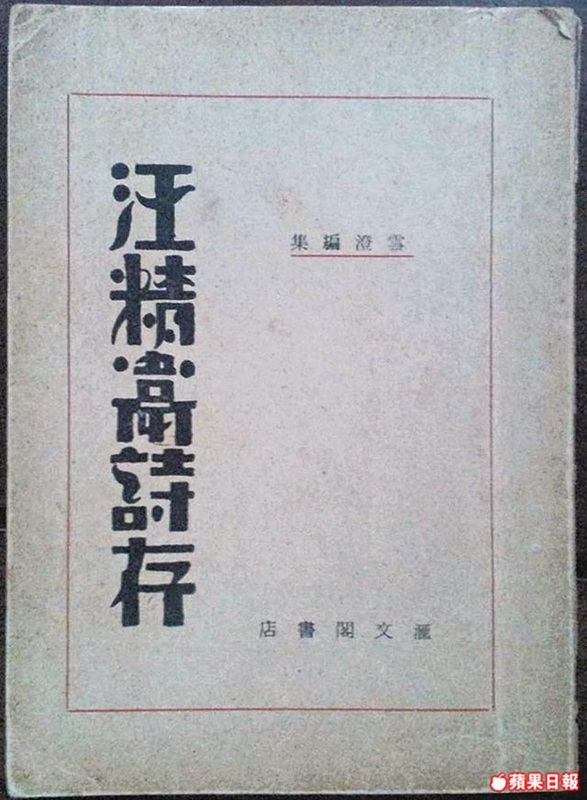
 RSS Feed
RSS Feed